真正摧毁教师教育热情的从来不是逆反的越轨学生,而是那一封封 " 零成本 " 的恶意举报。作为基础教育的一线老师,小 A 在短暂的一年教龄中如同尝遍了人生百态,从踏入课堂的坚定与激情到如今的徘徊与犹豫,小 A 逐渐变得 " 不敢管 "" 不愿管 "。
一、H 校的生源和师资
H 校是中部山地地区一所民办县域基础教育全覆盖的学校,该校高中部共设置了 69 个班级,高一 23 个班级,高二 20 个班级,高三 21 个应届生班级和 5 个复读生班级,学生数量超 3000 人。其学生大多来自本县域内的周边乡镇,学生成绩基础差,近乎 80% 的学生未达到县域公办普高学校录取分数线,学生对 " 差生 " 等标签的自我认同程度高,大多数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,学习习惯差。
该校共有 220 名教学及行政老师,校内整体师资差异较大,教师年轻化结构突出。从学历上看,所有教学老师均毕业于本科及以上院校,其中 138 人毕业于省属重点及以上大学,9 人具备硕士学历。
从资历看,教龄差异大,教龄不足五年的教师占比超一半,其中 148 人于 2017 年及以后毕业,尤以毕业 5 年以内的青年教师为主。从年龄构成看,30 岁以下的老师有 95 人;此外,学校返聘了少量从公办学校退休的优秀教师。
二、为何教师成为高危职业?
小 A 是 H 校高一某班班主任兼科任老师,在进校的短暂一年里,所在年级近乎每个班级都发生过安全事件,这些事件包括同学间打架斗殴、服药过量引发的自伤行为、锋利工具割手腕的自伤行为、私自逃课逃学等,这些安全事件让班主任和科任老师都尤为头疼。
在和同事的沟通交流中,小 A 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" 现在的学生真难教!稍微多管一下,就认为你在针对他了。"" 班主任就是全职保姆,什么都要管,不仅管学习、安全、心理,还要管吃穿住,不仅在校时间要管他们,学生放假了,家长还要求你打电话监督学生学习。"" 现在的家长们都很宠孩子,经常会发微信问我,学生为什么没有吃饭?" 从漫不经心的吐槽中,小 A 听到了越来越多的老师对本职工作的无奈之感。
然而,事情远不止如此,作为一线教师,小 A 耳闻目睹了身边老师的诸多遭遇,比如他们时常花费大量时间处理越轨行为的学生,如扰乱课堂秩序,不尊重科任老师;不遵守校纪校规,肆意妄为,屡教不改;上课或就寝时偷用手机;在校时间逃课或偷摸越墙外出 …… 有家长不配合工作,需要家长到校处理问题时,家长不处理不配合;遭到家长的恶意举报,被领导拉去谈话 …… 诸多事件让小 A 发现,如今的教育已今时不同往日,教育生态也与以往迥然不同。
究竟是什么在改变?又为何让老师时常感叹自身职业的高危性呢?
教师一直都是教育行业的先锋,备受敬重," 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 " 是大家共同认可的尊师理念。然而,当今,网络化深度发展的背景下,教师职业的认可度却在逐渐降低,年轻的小 A 在班上说出这句话时,引来的却是学生的讥笑和不以为意。
这种变化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,本质是教育主体间的权责失衡。以往,在信息相对闭塞的环境中,教育奉行的是 " 棍棒底下出人才 ",家校关系或师生关系的天平更多倾向于校方和教师,作为底层人跳出阶层的唯一途径是读书,学生只得依靠教师获取信息和增长知识,其传道授业和管理方式被普遍接受并认可,所以只要是不会带来皮外伤的打骂,大多都会获得家长的支持,教师与家长的矛盾也微乎其微。
然而,随着网络传播信息速度的加快,在信息爆炸时代,教育关系的天平开始倾向家长端、学生端,毕竟教育行业接连爆出 " 重拳体罚 "" 异性侵害 " 等丑闻,让以往对教师的信任崩塌,社会大众开始不信任教师,担心自己的孩子遭到身心伤害。于是,政府学校等出台了多种举措,完善举报机制,监督教师行为。
其本意是通过社会监督来加强教育质量,保护学生身心健康,推动教育透明化,但随着机制演进,监督逐渐变了味;其次,各大网络博主对教育方式的吸睛解读,让家长深信不疑,甚至一度认为自己是教育专家,因此对教师的教学和班级管理产生质疑,这导致少数家长稍有不满,就向领导或教育局举报教师,或者在社交软件上夸大歪曲事实。
校方在接到举报信息后,高度重视,会以最快速度了解情况,找到涉事老师谈话,从年级组、学生等多方面了解,查证该老师是否有违师德师风。校方的快速响应能把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,但遇到被诬告的情况时,与涉事老师的谈话会极大影响老师今后任教积极性,让老师选择 " 躺平 " 式的上课方式进行自我保护。
举报机制下的社会舆论和法律风险让老师自危,留痕工作成了唯一可以自证清白的证据。小 A 隔壁班的班主任因为在午休时间没有回复家长信息,家长便直接将该班主任举报至校长处,认为老师不负责,不关心甚至针对自己的孩子。而实际情况是学生上课扰乱课堂秩序,班主任在多次教导后仍不改正,便将情况告知家长,家长偏袒孩子,给他找各种借口。
班主任见沟通未果,为防止矛盾升级,就借口其他事情,待双方情绪平复再作沟通。但家长大中午又继续发来消息,此时,处于休息时间的班主任自然没有看到消息。起床后,该班主任被要求向领导说明情况。虽然了解情况的领导并没有责怪老师,但家长的这一行为让本就加班的老师失望,产生" 或许躺平点,就能少点麻烦 " 的想法。
当然,这类举报并非个例,全国各地,类似的举报事件层出不穷。西南一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数据显示,2024 年 1 至 8 月,该局共收到 128 条举报教师的信息,经核实,仅 7 起举报基本属实。在不实举报中,多有恶意举报,如编造教师体罚、辱骂学生等情节。" 零成本 " 的举报机制虽然维护了家长、学生的权益,但恶意且不符实际的举报,伤害的是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,弱化了教师的责任感。
工作及责任泛化产生的超额工作,严重影响着教师的身心健康。教师的工资与学校安排的各项任务、学生的课堂表现、成绩等紧密挂钩。
H 校考核严格,日常坐班打卡是考核教师工作的重要指标,H 校的考核简单粗暴,工作日需要在指定时间完成每日 4 次上下班打卡,缺卡一次,扣款 80 元。此外,教学工作及学生课堂表现等也是重要的考核内容,在 H 校,查班老师、各层领导每天至少巡查课堂 7 次,这就倒逼老师必须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任务。
一线老师,尤其是班主任的工作量很饱和。除了完成教书育人、传道授业的本职工作,还要兼顾好各类行政事务、家校沟通、学生安全等事宜。原是为了增强教师的职业素养和师风师德而召开的工作会议、开展的活动,却在多频率和长时段上变了味,逐渐偏离初衷,演化为形式主义和敷衍了事。
例如,小 A 参加的会议有:年级组教师例会,全校教师工作会议,年级班主任例会,全校班主任月会,备课组集备会议,每逢考试周还需要参加学科分析总结会,并组织班级教师会议等。平均下来,每周几乎都会参加一场会议,会议时长从十几分钟到三四个小时不等。
每场会议的主题大体相同,这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教师备课的连续性。行政性的表格任务下派得很多,每次填写的内容几乎都是学生基本信息,但上交的责任人又不同,这种重复性的工作很容易消磨工作热情。
除了日常教学,学校还极其重视学生的安全问题。学生是安全的主体,安全问题是学生的头等大事。无论何时,发觉学生存在情绪问题和逃课状况,老师都需要第一时间上报德育领导并主动寻找学生。
H 校的学生在返校当天,会经历第一次安保检查,由值班老师、门卫、生活老师共同构成的安保检查组,对学生的返校物品进行检查。返校当周,班主任会利用午睡、晚寝、学生上课期间,对教室、宿舍进行逐一检查。虽然会经历多重检查,但对于想尽办法想自伤的学生作用较小。
仅以小 A 所在的年级来说,高一学年里,23 个班级均发生过大小不等的安全事件。每逢出现安全问题,领导的问询是必要环节,纸质留痕及处理也是教师对自我的一种保护。
很多家长认为,把学生送到学校来,学生的一切问题均由老师负责。甚至有部分家长在接到老师给出的希望家长配合的建议后,依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,不以为意,认为自己的孩子出现越轨行为都是老师没有教好,总是把一切问题都甩锅在老师身上。小 A 和身边的同事在重压面前,身体素质逐渐降低,失眠、焦虑、结节、气虚等都成了老师的通病,给教师的身心带来影响。
教师人身安全与职业风险的考量,让老师 " 不敢管 "。和小 A 同办公室的某班班主任,时常接到科任老师对学生的反馈,该班一学生上课时写小纸条被任课老师发现,任课老师下课后第一时间将纸条交给班主任,并告知班主任事情经过,发现该生的纸条有早恋倾向,还未等班主任处理,学生在晚自习时主动来到办公室,要求班主任退还纸条。
班主任试图以讲道理的方式让学生意识到问题,但没几分钟,学生没了耐心,就用脚踢办公桌,从老师桌上夺过纸条撕碎,撒在办公室,紧接着直接从班级手机存放处里寻找自己的手机,并扬言 " 不读了 ",然后就跑出了办公室。
因为该学生个子高大,又是班上的问题学生,办公室里只有 3 个瘦小的年轻女教师,她们担心插手事件后,学生情绪更激动,会伤害班主任,只得求助年级主任来处理。教师的这种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,学生伤害老师的新闻也真实存在。虽然这种极端的学生很少,但老师心里也开始泛起了嘀咕,自己作为家里的顶梁柱,不敢用自己的生命在工作中冒险。
校方的责任规避和劝退机制,让一线教师缺乏避风港湾,归属感低。同事 B 是从公办学校退休下来的优秀教师,教学能力突出,带过多名学生考进名校。返聘到 H 校后,B 依然虚心学习,认真听年轻老师的授课,以采取更有效的教学方式提升学生成绩。
然而,由于该老师授课未采用 PPT 形式,学生已经习惯 PPT 教学方法,这使得部分学生难以适应。少数家长了解到情况后,将问题向学校领导反馈,但领导未重视该问题,在家长的多次反馈后,B 突然被劝退。本是一代名师,最后却以 " 教学能力差 " 劝退而结束,当其他老师知晓情况后,不免会担心自己的处境。
三、搭建平等的对话体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
零成本的举报机制初衷是优化教育,但在当下随意举报的教育生态下,倾向家长、学生的天平让一线教师在夹缝中生存,如何才能改善这种局面,或许搭建平等的对话体系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
家长与学校、教师之间的矛盾根本在于教育主体间权责的失衡,这种失衡状态导致教师与家长无法进行平等对话。现行的举报监督机制是单线条的家长对教师、学校的监督,一旦出现举报,涉事老师只得以留痕证据的方式自证清白,但这种举证多少显得有些苍白无力。
出现问题时,处理者实事求是,不先入为主地认为举报人是弱者,而是以更加客观中立的立场处理问题,不让教师成为 " 背锅侠 ",多听取意见,对恶意举报的行为给予适当惩戒,从而减少恶性举报的频率。
对于教育管理和学生惩戒的细则,相关部门以更明确详细的方式让教育者清晰明了。此外,沟通与相互理解是减少冲突的要点,家长与教师之间相互多一些包容和责任理解,这才能减少社会的不信任。
学生是家长与教师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,教育工作也紧紧围绕学生而展开,家校师三方是共同体,而不是矛盾体。只有彼此间多一份尊重与理解,教育的纯粹才能被重拾,教育行业也才不会发生信任危机!
转载请注明来自北京夏犹清建筑装饰,本文标题:《恶意举报,正在摧毁一线老师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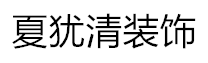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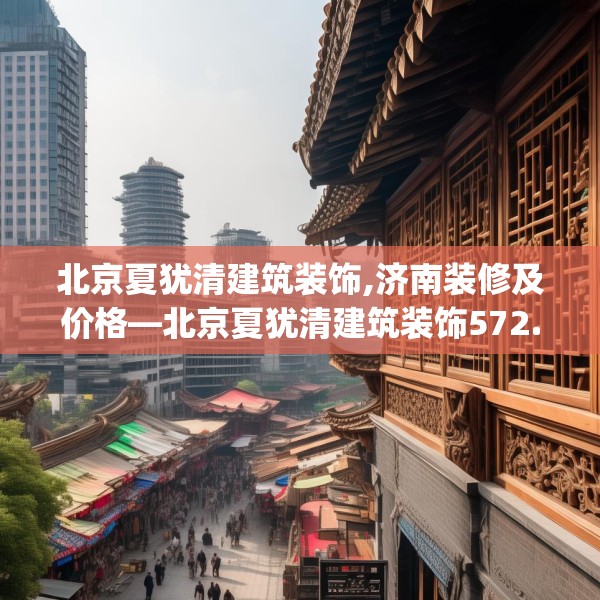



 京ICP备2025104030号-1
京ICP备2025104030号-1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